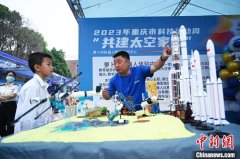我叫苏芗远,出生在这座城市的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现在回忆起来唯一能够记忆的起来的就是深夜时刻楼下的路灯,它陪我度过了很多很多个无聊又孤单的夜晚。
有的时候我很好奇觉得是不是大人的世界真的那么不一样。
因为他们会在天色微亮的时刻出门,因为他们会带着夜晚静谧的薄雾笼罩的街道中踽踽,他们的背影坚决而轻快,他们的心灵沧桑却疲惫。
他永远都记得那个不因为沉闷而发酵的年代。
阳光慵懒地从方格子的窗帘的缝隙中倒坠下来,照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又射向地面,被贪婪的空气吸收,就像芗远的梦一样香甜。
因为那正是三年前。
芗远的妈妈和爸爸刚刚因为吵吵闹闹着离婚。
而他自己,也正式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家’。
三年前,与他们不远的地方一副窝囊的样子但却有着清秀面容的唯正在被他专制的母亲痛骂:三年前意气风发的基特正睡眼惺忪准备离开曼哈顿繁忙的公寓出门:三年前还仅仅在狭小逼仄的出租屋容身的侦探德科又捡起烟灰缸里燃尽的烟头,抽着那有浓重发霉味道的烟草,紧裹着长着厚重补丁的衣服。

但是,有人说过,时间之轮总是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匆匆流转不息,每一个故事我们都能够找到开始或者结尾,而不管它是快乐还是悲伤,简单还是啰嗦。
因为这样的事情重复过太多遍。
但是故事却必然要有一个开始,而这,就是故事的开始,或者结束。
芗远是被窗外恼人的知了叫声吵醒的,还有一样烦人的英语老师,嘀咕嘀咕的讲课声,周围的同学不是像他刚刚那样睡眼惺忪地见周公,就是一脸正经对着老师露出他们那些白痴般的笑容。
“真是无聊的一天啊” 芗远从来都对班上的课程兴趣缺缺。
他碰了碰边上还在香甜的梦境中的黄而,却没有得到回应。
不过想想也对,这个自称“觉皇”的家伙,芗远才不信他在下课之前能够起来的。
芗远跟嘀咕嘀咕的英语老师比划了一个上厕所的手势,借机就跑到了外面去。
9月的阳光依然是大大的一团,晕染得天空亮得刺眼,芗远顺着楼梯走上了5楼的露台上。
因为他们的学校是属于全封闭式的教学,平时根本都不让出入教学楼一步,于是,顶楼的这个露台就成了,他们这些在被逼得发疯边缘的高三学生们活动兼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虽然不大,不过好在是整栋大楼唯一没有安排摄像机的方。
芗远他们几个时常在这里一起抽烟什么的。
倒也没有学坏怎么的。
只是年轻而空旷的时光里总得找到一些可以寄托的东西。
况且。
芗远又从来不是老师的乖宝宝啦。
大山请假回家了,白驹也学了艺术,只有我和黄而这个大肥猪还在这么烂的地方混着,诶……”芗远无聊,只能自己跟自己嘀咕着,还想着,也许抽完烟还有再回进教室里面睡一觉才是正经。
毕竟,今天晚上还要出去玩的啦。
芗远扔掉烟,对着玻璃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被汗水浸得有点发黄的白衬衫.芗远觉得自己笑起来的样子还是蛮帅的。
然后伸手,拉开了面前闪着银色亮光的门罢手。
“等等,银色的门把手,我怎么记得应该是铁的呢,真是烂记性的说。
”这么想着,一阵天旋地转的,坠落感。
“上面好像还有字呢”这是芗远最后的想法了。
而几乎与此同时的玲子,正在过着自己的第二个生日,似乎是上天给她开的玩笑。
身为孤儿的玲子在她长达二十年的生命中,只有五次过生日的机会。
其中的四次还是和她的养父母在不可记忆的小时候。
长大后,大概是由于性格的缘故,当她身边的人秘密计划为她庆祝生日的时候,玲子总是会诡异地提前发现,并且表现得坐立不安甚至到最后簇簇地发抖。
于是计划就始终是计划,从来也没有实现过。
“诶,也许几年前那件事对她打击太大了吧。
”玲子常能够听到同事们之间的窃窃私语。
“是啊,无论是谁在被亲生父母找到并度过第一个生日的当天被人入室抢劫未遂然后父母双亡,都是会这样的啊,更何况,最近蔬菜价格又上涨了,生活压力这么大。
” “是啊,是啊,我还听说啊,就是她自己,那天都被侵犯了,你说叫一个女孩子怎么做人呀。
” “对了,他们还说呢…” 背后的议论随着同事们的渐渐走远而变得悄不可闻。
然而天知道,玲子有多么不想听到这些。
只是听到了也会觉得无所谓吗?不知道为什么,不幸始终缠绕着她,山田玲子。
玲子真想不顾一切的痛骂他们,与一切无关却总是用鄙夷的语气评价着一切的那些人。
玲子像往常一样边在心底埋怨,一边参照往常的习惯去自己的办公室里休息,却不知道,自己正推开一扇不一样的门。
何妈妈有些着急,因为他的宝贝儿子现在还没有回来。
眼看天色渐渐从橘黄到墨蓝,第11次拿起手表来看时间。
“这个死小子,不知道又是到哪里鬼混去了,真是不让我省心了。
多大的人了,不知道我跟你王阿姨都约好了嘛。
回来我收拾不了你了还。
哼。
” 何妈年岁大了,就有了些啰嗦的毛病。
这也许正是唯不愿意早点回家的原因吧。
“叮——”门铃声响,何妈急急忙忙跑到门口,开门果然是唯。
宽大的裤子和浆洗的有些发白的套头衫,胡乱地搭在肩膀上面,斜跨着书包,像以往一样慢悠悠地走进来。
“你这个死孩子,让你早些回来,让你早些回来,你不回来,是不是等我死了你才肯回来。
你就跟你爸一个样。
不回来·,不回来,有种你就永远不回来啊。
”何妈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快点快点,回来了就赶紧吃饭,吃晚饭就去你王阿姨那儿,我告诉你,这回你要再敢向上回那样没大没小,看我怎么收拾你。
” 絮絮叨叨的有一大通。
唯不由得有些不耐烦起来,挥挥手。
看到儿子还是这个样子,何妈更加显得焦急。
“不爱听,不爱听是吧,嫌我墨迹是吧,不爱听你倒是争点气啊,你看看你,这都毕业几年了,你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了么,一天到晚的鬼混,也没看你混出什么名堂来。
上回本来好不容易托你王阿姨给你找了份工作,你还那种态度。
你倒是厉害了,你知不知道,你老妈有多辛苦啊。
多大的人了,还让我操心。
”唯有些痛苦的紧了紧眼睛,可以知道老娘在这个时候是最最不可理喻的,心中倒是打定了注意,坚决不开口,只吃饭。
江海的夜色迷离,黑得很快,他们娘俩就坐到了离他们家不远的王阿姨家里面。
王阿姨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南方柔软的语调都掩盖不了骨子里的刻薄。
在唯爸爸还在的时候,他们是邻居,只是后来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唯的家道中落,于是王阿姨就不愿再与唯一家人来往。
这次何妈舔着脸来求她,王阿姨好像嗅到了来之不易的机会,摆出了露八颗牙齿的阴险笑容。
“呦,这不是老何嘛,多长时间不来看我了啊,哈哈哈,啊,小唯也来了啊,来来,坐,快坐,给你们尝尝孩子他爸从‘福建’带回来的铁观音。
哈哈哈…”笑的声音只有在猫头鹰被踩住脖子才能出来的声音。
唯突然感到一阵心烦,像王阿姨问了厕所的位置,就要去避避风头。
把手还是银的嘛,真奢侈… 2012年5月9日 吉哈特最近有些郁闷。
噢,不,应该这么说,吉哈特总是有些郁闷。
这已经是他第几次被甩了,3次?5次?也许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吧。
其实吉哈特长得在平常人眼中看来也算是英俊潇洒的,只不过他的女朋友总是被更多个比他还有型的男人,或者女人抢走。
也许是因为这个,吉哈特总是自嘲说,自己身上天生就有一种倒霉蛋的味道。
比如现在,被漆成红色的储物柜,和自己沾满油漆的手。
吉哈特从来不怀疑是有人故意使坏什么的,因为他知道他们是要对付旁边新来的小子班恩的。
对此,他除了能够怀疑自己的坏运气之外,还能埋怨得了谁呢?刺耳的朋克乐曲是他们这所倒霉学校的上课铃声。
倒霉的吉哈特不得不满手油漆的去上课。
直到推开那扇门之前吉哈特还在为怎么应对教室里的那些必定又会嘲笑他倒霉的坏小子而烦恼。
直到他看到教室的门不知什么来时候换上就了银色的把手。